
臨川一中北校門外的“陪讀小區”
去年8月,張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選擇——放棄穩定的工作,陪兒子讀高三。
同一時期,楊金梅夫婦一狠心關掉了在北京開了十幾年的門窗店,跨越了大半個中國,陪高中的兒子回到江西老家。
王芳菲放棄了“30萬年薪”副總的工作,操起十多年沒摸過的鍋碗瓢盆,陪獨生女兒度過高三這一年。
而早在8年前,席雯就辭去小學教師一職,帶著3個孩子,從廣東一路北上。陪讀的她送一個孩子上了大學,眼下還剩下兩個孩子。
來自四面八方的她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地——有約萬名學生的臨川一中。這個地處江西中部的中學,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,有二三十名學子考入清華北大,最多時占全省清華北大名額的三分之一,被稱為“神話中學”。
學校所處的上頓渡鎮也因此被激活。這座小鎮因為工業稀少而天空湛藍,目前在鎮上發展最快的產業是房地產。在臨川一中三個大門外,分布著一圈冠以“錦繡前程”“一品世家”“名人公寓”“學府世家”之名的小區,防盜窗上懸掛著“包吃包住”的條幅。每年開學那幾天,上百名房東在學校門口舉著牌子,就如在火車站接人一樣,尋覓租戶。
圍著“巨無霸”學校輻射開的,是牛奶店、果蔬攤、雜貨店、書店、快遞店、理發店、通信服務網點……所有的店鋪與學校的作息保持著同呼吸般的運作。
在全校萬名學生的身后,是數千個陪讀家庭。她們被稱為現代版“孟母三遷”。這些“陪讀家長”有著共同的口號——“一切為了孩子”。
“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,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”
4月22日清晨6點,天空已經明亮,3個孩子的房間靜悄悄,張英的手機鬧鐘已經響了。她常常比鬧鐘醒得還要早,這是來陪讀的第一天“落下的毛病”,生怕錯過了孩子起床的時間。
9個月前,她辭了工作,從相距200多公里的縣城趕來,專門照顧升入高三的兒子小林和另外兩個同鄉孩子的飲食起居。

午休時的教室
盛滿三大碗粥,剝好水煮雞蛋,睡眼惺忪的3個孩子才打開房門,一個接一個地去洗漱,吃早飯,離開家門。
張英家租住在臨川一中新校區北門附近,離學校只有一墻之隔,從四樓的陽臺上望出去,可以看見學校的食堂、體育館和宿舍樓,也可以看見學生從蛛絲密布的巷子、樓門走出來,像無數小溪流匯入大海一樣,匯入這所學校。
這是4月一個平常的早晨,但對張英而言,距高考又近了一天。盡管家里沒貼出高考倒計時,她總能準確地回答出距離高考的天數。在她看來,高考是一場“戰斗”,“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,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”。
他們無需為洗衣服、做飯、洗碗這些瑣事操心,也沒細想要去哪座城市、讀哪所學校哪個專業,眼下他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:學習。
在臨川一中,學習這件事,被嚴絲合縫地安排進了學生的每一分每一秒。
學校的作息時間表就像一把小尺,讓張英每一步行動都要卡在合適的時間,精確無誤,才能保證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,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轉。
此前從事文書工作的她,為此專門寫了一張“注意事項”的紙條,貼在廚房門口。在她偶爾需要回原單位辦事時,需要用這張單子提醒來代班的妹妹。
在這張列著時間的小紙上,每一步都必須與學校的時間表保持在10分鐘之內的差距。這意味著,中午12點放學后,12點10分必須做好“三菜一湯”放在飯桌上;下午5點15分放學后,必須在5點20分保證飯菜上桌。
因為到了飯點,除了少數學生在食堂吃飯外,幾千名學生會從教學樓涌出,向東南北三個門走去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緩慢,3個孩子要花近10分鐘才能回到一墻之隔的家。
看著潮水般的人流,住在北門外第一排樓房的張英才覺得,自己租這個房子是“很英明很實惠的”,雖然她有時會抱怨自己住的這片區域是農民的拆遷房,沒有形成小區化管理,20棟“握手”樓還經常停水。
與這片簡陋的居民區相對的,是學校南門外的新式小區,有小區大門、圍欄,樣式規整的高樓間有綠色草坪。盡管“好壞”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與學校的相對位置來決定的。比如校門正對面的小區,就是“最好的”,其次是斜對面的。離學校越近,房租價格越高,最貴的一年租金兩萬多元,在這座人均GDP約3萬元的小城里,房東“完全就是躺著賺錢”。
除了出租房屋、代管學生,在臨川還有一種賺錢的方式——開出租車。
“撫州沒什么流動人口,就是靠這幾個學校。” 出租車司機老張說。一到放學開學期間,火車站汽車站到處都是人,“出租車拉都拉不完,一下就能走幾十輛,一天頂3天。”
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圓向外擴散,越靠近學校,人口越密集,離得越遠,越荒涼。在一些小區的售樓處,都用紅色的大字打出“學府”“名校”的名號。
高二學生家長鄭楠告訴記者,她早在三年前就考慮在臨川買房,當時兒子還在家鄉讀小學,家鄉宜黃與臨川同屬于撫州市。
她打算,等兒子讀完后,還可以把房子租給其他陪讀家長。但丈夫沒有同意,這個計劃擱淺了。兩年后,兒子順利入學臨川一中,“本來一套房子30多萬元,兩年的時間就多了10萬元”。
“我們那個縣,鄉下的人來縣城陪讀,為了孩子把田都荒廢了,到縣里面來買房子。縣里面的人就到市里買房,市里的人就到省城,每個地方都一樣。”鄭楠說。
“高考第一是狀元,采訪、上報、掛橫幅,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”
送小林來臨川讀高中,是張英夫婦在孩子上初中時就設計好的路。為此,他們拒絕了留在原籍讀書2萬元的物質獎勵。
在學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廣場上,幾張大紅色的“喜報”欄從去年立到今年,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華北大學生的名字,以及考上外省重點院校的學生名單。
校長王昱不喜歡把自己的學校和衡水中學這類“超級中學”比較,他認為這是“片面地看到我們高考成績好”,他更喜歡和記者談論學校這幾年大力舉辦的文體特色活動。

學校附近的小廣告
“片面地追求升學率,肯定是不合適的,”校長王昱說,“但是有升學率是一所學校的榮耀,真不是犯罪。一個學校如果連升學都管不好,它絕對談不上素質教育。”
這座小城,曾走出湯顯祖、曾鞏等歷史名人,但是家長更津津樂道于一串數字:2016年,江西省理科狀元出自臨川一中,38名學生進入清華北大,而清華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額僅有166個。每年高考成績出來,這個數字都會被地方媒體大肆報道。
這場逆襲以2002年為一個分水嶺。在這之前,臨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,四五千名學生以當地生源為主。2002年,撫州市成立了臨川教育集團,將臨川一中、臨川二中和撫州一中三所學校納入集團進行統一管理。據當時媒體報道,集團剛成立時,政府鼓勵這幾所中學面向全國招生,還成立專門的宣講團四處擴大影響。2004年,12名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,隨著名氣的擴大,短短5年,包括復讀生在內,臨川一中已有11000人。
2016年考入清華大學的熊峰回憶,在他中考那年,縣里前10名,都會接到臨川一中打來的電話,提供免學費免房租的優惠政策。
在過去幾年的臨川一中,這些外地的優等生源往往會構成“喜報”上的主力軍,在校長辦公室里,一面墻壁的正中懸掛著一副牌匾——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”。
“臨川一中都是看清華北大,不看一本二本。不是說每個人都為了考清華北大,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來,人家就會說,這個學校真的很好。”一位陪讀家長告訴記者。
招租也打著類似的名號。有的專門將“狀元樓出租”幾個字放大,在括號中寫著“如果考上狀元,租用費用全免”。有一戶人家,在陽臺的防盜窗上掛上一條巨大的紅色橫幅,慶祝租在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。
張英租住的樓房,就是2008年新校區搬遷時,當地農民建造的。房東小王說,“學校開始造,我們也開始造”。還沒修好門前的水泥路,就已經有家長過來住,這幾年租戶從未中斷過。“我們希望學生考得好,這樣就有更多人來住。”
這里流傳著許多故事,有的人在這里待了八年十年,只為了把3個孩子都送去大學;有的人辭了年薪幾十萬的工作,陪孩子最后一年;兩位來自別處小縣城的學校老師,在高三那年,母親請假一年來這里陪孩子讀書,父親留在家鄉的學校為妻子代了一年課。在很多人眼里,全家再大的事大不過高考。

高三學生在晚自習
帶著3個孩子陪讀8年,把大女兒送進北京大學的席雯,就是“媽媽幫”里活生生的例子。
2008年,席雯辭去廣東一所小學教師一職,帶著3個孩子遷往臨川。她講到陪大女兒時,晚上洗腳水都要打好,讓她邊寫作業邊泡腳。有人說她“你太慣孩子了,以后自理能力很差”。
“她讀書那么累,我幫她做一點有什么關系。”席雯毫不在意地說。不過她馬上舉例說明,自己女兒上北京大學后,會做菜,回家還會幫她帶弟弟妹妹,“很獨立”。
楊金梅的小兒子還在臨川一中讀高一,她就來陪讀了。去年夫妻倆關閉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幾年的門窗店,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,因為“泉州到撫州有直達的高鐵”,方便看孩子。
她還記得,兩人送兒子回來讀書的那天,她看到許多家長在這兒陪讀,問兒子要不要留下來。兒子心疼他們放棄生意,說“不要了”。楊金梅坐在車里,“眼淚一路從江西流到了安徽”。那天,兒子躺在床上,用一本書蒙著臉,她猜測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。
最后她決定陪讀,是因為不愿小兒子重蹈大兒子的“覆轍”。大兒子從小在外婆家養大,初中讀完就出來打工,“走到彎路上”了。
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險的信號。相比學習,兒子更喜歡打籃球,看到嶄新的球衣,“眼睛都發亮了”。然而剛剛過去的期中考試,一向數學成績優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。
這樣的成績會錯失“零班”。而進了“零班”,就相當于一只腳踏入重點大學的保險柜。
進入高二,40多個班級會被分為“零班”、A班和B班。“零班”的學生將享受最好的教師資源,“連學習資料都是免費的”,高考時,由學校安排車接車送。
一位父親稱根據自己的長期觀察,“下課后,如果這個班教室門口幾乎沒有學生出來玩,那就是零班;如果出來的不多,就是A班,出來一堆人,那肯定是B班”。
“零班”不是用牌子掛出來,而是敲打在每個學生,甚至每個家長的心上。
一位臨川一中走出的學生在網絡上寫道,“零班”老師喜歡說,“我們缺的是清華北大,武大廈大之類學校誰考上對我們不重要”“高考第一是狀元,采訪、上報、掛橫幅,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”。
王芳菲的女兒不在“零班”,“有時候女兒回家會說,你們這些大人,早就把我們分成三六九等了。”但這位愛讀龍應臺作品的母親安慰女兒,“你走完人生該走完的路,以后不會后悔就好。”
因為孩子沒考好,楊金梅的丈夫著急地打長途電話過來,“兒子,難道我和你媽媽這樣的選擇是錯誤的嗎?”重話一出口,他又有些后悔,偷偷打電話給老婆讓她安慰一下兒子。
小林在文科“零班”就讀,去年暑假,張英看到這塊上重點大學的紅榜,會和兒子開玩笑,“什么時候你的名字能寫上去咯?”但是今年她從來不說這樣的話,“不能給他太大的壓力”。
“高三了,也該來了”
去年8月9日,是高三開學的日子,也是張英來到上頓渡鎮的第一天。此前,專門雇了一位農村的親戚照顧幾個孩子,可“高三了,也該來了”。
許多的陪讀家長都遵循這樣的軌跡,“高三了,也該來了”。
王芳菲的女兒升入高三,打電話告訴她,“媽媽,無論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”。

學校門口的小書攤
“小孩的路還很長,萬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學校,有怨言怎么辦。”一直奔忙于職場的她,從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臨川讀書,自己在外地打拼。作出這個決定時,幾乎沒有人支持她。但一想到孩子的未來,她還是心軟了。
在臨川單獨租了一間60平方米的小房子,王芳菲從十多年沒怎么摸過的鍋碗瓢盆開始,一點一點融入女兒的生活。
如今張英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個鎮子的節奏。
樓下牛奶店,即使顧客忘記帶購物卡,老板娘也可以先賒著賬;小超市里,零食種類不斷更換,滿足孩子多變的口味;步行20分鐘的菜市場里,野生黃鱔60元一斤,她買起來毫不猶豫。
但在臨川,她依然被打上“外地人”的標簽,一次在菜市場買肉時,她和同行的陪讀媽媽被不斷擠到后面,朋友著急了,嚷道:“你們不能這樣對我們,你們不還是靠我們這些外地人養活。”
進入高三最后一個學期,張英明顯感覺到,“壓力更大了”。
考試多了起來。摸底考、省聯考、超級中學大聯考、穩派名校聯考、還有大大小小的月考……每次考完,就是孩子情緒的低谷期。
在飯桌上,3個孩子中一個耷拉著腦袋,沉默地扒著飯;一個搖搖頭,把碗一推,說“吃不下,沒食欲”。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則會拍著桌子,大叫著“我要炸學校”。
張英開玩笑“吃飽了才有力氣炸學校”,半哄半騙地讓孩子們好好吃飯。
私下里,她專門拿個本子記錄菜譜,68個菜樣,前面打著勾的,是她暗自觀察出受歡迎的菜,比如“排骨蒸芋頭”“紅燒帶魚”等。
夏天到了,她堅持要把菜燒得辣一點,“這樣孩子們才有食欲”。“談心?都不怎么談,他們的壓力已經夠大了,” 張英抓起一把紅辣椒,放進滾燙的油鍋中,“家長只能每天盡琢磨吃的了”。
如今在清華大學讀書的熊峰記憶深刻,高三快臨近高考時,他有幾次模擬考試沒考好,“心里不太痛快”。晚上寫完作業,他躺在被窩里玩手機,被母親發現了。
不動聲色的母親,直到第二天中午,才邊吃飯邊淡淡地說,“快高考了,不能馬上松下來”,并說自己的手機壞了,借你的手機用一下。熊峰立馬交出了手機。
直到畢業之后,他才知道,那幾日母親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現出什么情緒,但是背地里十分擔心,“整夜整夜睡不好覺”。
“我覺得,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”
4月30日,高三年級要開家長會,提前了兩日通知,張英和在家鄉工作的丈夫林強商量了一下,還是決定由林強趕來參加。
相比于母親,在老家的“留守父親”更像候鳥,每個月來看望兒子一兩次。當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顧孩子時,他們肩負著賺錢的責任。張英曾算過一筆賬,包括房租、菜錢、水電費、煤氣費、工錢等所有開支在內,3年來一個家庭大約要花費10萬元,培養一名臨川一中的高中生。
家長會那天,林強沒訂到他經常住的、鎮上最豪華的酒店。他打聽到,還沒到5月,鎮上的酒店已經公布出高考當天的房價,比平日提高了近兩倍,而且“最好提前兩個月預訂”。快遞店門口也打出了“高考生寄貨大優惠”的廣告。
張英的同鄉華麗經歷過這些,今年是華麗的兒子第二次迎戰“高考”。去年一放榜,兒子掉了一本線,什么都沒說,直接給父母發短信,說“我要復讀”,父母二話都沒說,只回復了“好”,又續租了一年的房子。
據說,高考那天,家長都來了,“車都沒地方停”,文科班的學生會被大巴接走,去臨川二中考試。在考場外等待的家長,會把校門前的一條路圍得水泄不通。
一考完,就有轟轟烈烈的“撕書大會”,“零班”不讓撕,但是會有人偷偷跑到別的班級門口,三下兩下就把書撕開,從樓上拋下去,還會有低年級的學生撿來為以后的復習做準備。這項活動常常會持續4~5天,比“百日誓師大會”壯觀得多。
林強已經打算好了,他對兒子說:“高考期間,我不會影響你,吃還是這樣吃,也不要加什么菜了,已經營養過剩了,要是堵車,我就叫朋友開電瓶車送你。”
教室前半部分的墻壁上,貼著近幾次的聯考、月考成績,班主任宣稱,5月的考試不會再貼出成績單,也不會發送給家長,“保持一顆平常心”。每個書桌上都壘著厚厚的一疊教輔書,按小林的說法,從外面看“連頭都看不到”。
廣播里響起了臨川一中副校長的聲音,這位副校長強調“這個月復習與家庭配合很重要”,還專門提到陪讀問題,“如果孩子覺得有必要,非常希望家長最后一個月來陪著他們,那么家長就應該放下手上的事情。如果他覺得沒有必要,或者家長實在抽不出時間,就要以平常的心態來對待高考。”
這位副校長頓了頓,又說:“高考確實是挺殘酷的,我們國內的高考,基本上是一考定終生。但我還是這么說,高考的勝敗并不能決定人的一生,我覺得,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。”
廣播聲音剛落,班主任走上講臺,開門見山地說,“這次考試起伏有些大”。她叮囑陪讀家長要讓孩子“平平靜靜,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擾”。接著舉了一些平時不起眼、高考脫穎而出的,以及平時很優秀、高考失敗的例子,來說明一定“不要輕易改變吃住環境”。最后她總結道:“這一屆肯定是讓我最感到驕傲的。”
家長會結束后,圍在班主任身邊的家長并不多,一位從廣東趕來的家長,焦慮地向老師詢問,自己沒辦法來陪讀會不會有影響。
回到家吃完午飯,張英夫婦走到兒子房間,關上門,林強一改往常和兒子打鬧的風格,語重心長地對小林說:“在學校里有什么苦惱的事,學習遇到什么壓力,適當和你媽媽發發脾氣都行,但也要顧及你媽媽的面子。”
最近幾次考試,小林發揮不穩定。“你以后上了大學、考研,我們都不管了,但是現在高三,我們還是要管。誰都考過,神仙都會重視,中國的體制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試,不要滿不在乎。”林強說。
如今在清華大學讀大一的熊峰說: “高考給了像我這樣家庭條件不是特別好的農村孩子一個機會。要是沒有高考,想走到更大的舞臺上,還是挺困難的。”
“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”
“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。”張英說。
傍晚是小鎮最熱鬧的時段,三五個陪讀家長圍成一圈聊天,不時抖抖腿驅趕蚊子;操場也漸漸接納接二連三到來的家長,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繞著走,操場旁邊就是燈火通明的教學樓——他們的孩子在里面上晚自習。
日子久了,陪讀媽媽們形成了自己的“小生態”。王芳菲報名參加了當地一個會計培訓班,每周去三次,打算好好學一學原來在上班時沒空學習的東西,為“再就業”打基礎。
在臨川“駐守”多年的席雯,“結拜姐妹” 13個。這群姐妹“一呼百應”,平時一起健身、跳肚皮舞、過生日、做飯。
張英常去汗蒸,一周兩三次。汗蒸房位于南門小區一處臨街的居民樓上,門口打著標語“請人吃飯,不如請人出汗”。在這里,相約去汗蒸是陪讀媽媽的一種“日常活動”。
這家汗蒸房是來自四川的李平和別人合伙開的,她的兩個女兒正在讀高三,“一個花了4萬8,一個花了2萬4”。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,來到臨川閑來無事,發現了商機,“來的基本都是陪讀家長”。

晚上10點放學的場景
她們組成了一個“汗蒸陪讀家長群”用來聯絡,常常有人因為“今天孩子在家”“老公來臨川”等原因取消行程。
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,擠不下20個人,一進去要灌下一大杯“堿水”,高溫逼迫汗水溢出,不到10分鐘就會滿身大汗,據張英說這樣“可以放松心情”。
熟悉的人漸漸多起來,相互間聊的話題依然離不開高考。
她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交換經驗,比如在網上看到高考那天,要穿“旗袍”,意味著旗開得勝,男人穿馬夾,寓意“馬到成功”。另一位家長馬上說,她考察過了,這里紅色旗袍賣得貴,“一件要300”。還有的母親說,考試當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雞蛋,“肚里有墨水”。還有人打聽過,高考那幾天,臨川一中老師和學生都要別上一枚毛主席像章。
這些被孩子們稱為“迷信”的做法,卻深受家長追捧。
“文曲星的生日”那天早上,張英專門空著肚子,“虔誠”地前去附近的“太子廟”朝拜。
在大殿門口,一名身穿長衫的僧人,被一群婦女圍著,他手中拿著圓珠筆和本子,記著學生的姓名、學校、年級,“點一次燈160元”。僧人介紹說,高考那幾日,準考證可以復印了拿到廟里來,為考生念經祈福。
眼下,李平急著轉讓這間汗蒸房,因為等女兒高考完了,自己也要離開這個地方。很多家長也開始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,“慢慢地一點點搬回家”。
看慣了人聚人散,席雯說,有的家長一直說著想回來,但有了新的生活,很少有人回來看一眼。也有家長離開時,“會扔一塊石頭在這里”,意思是今后再也不會回來。
開家長會那天,離高考只有37天——學校里各處都能看到倒計時器,高考已經進入了最后的沖刺階段。
在45個高三教室里,倒計時有的被寫在前方黑板正中央,有的被寫在后方黑板上,還有的被學生用鉛筆輕輕地描繪在桌角上。
無形的倒計時在很多人心里。張英經過教學樓,迎面走來素不相識的兩個家長,沒有寒暄,大聲詢問:還有幾天高考了。
“不到四十天了。”張英突然心里一驚,她加快了腳步。這天回家有點晚了,牛奶還沒給孩子熱上。
(應采訪對象要求,張英、楊金梅、王芳菲、席雯、鄭楠、華麗、李平均為化名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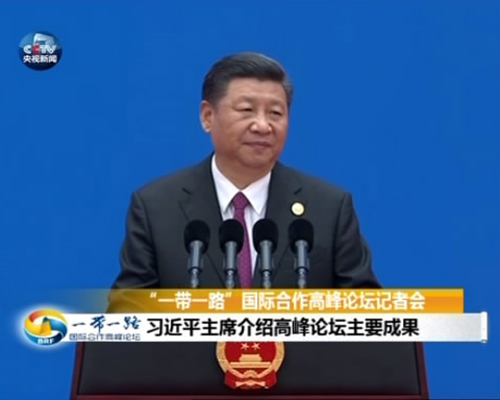 習近平主席介紹高峰論壇主要成果
習近平主席介紹高峰論壇主要成果
